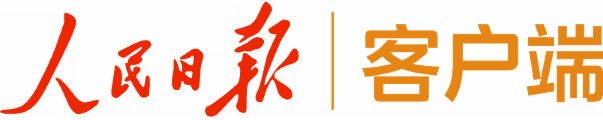5月7日,第二届中国凌家滩文化论坛开幕,200余名国内考古界专家学者齐聚安徽马鞍山,为凌家滩文化研究建言献策、凝聚共识。同一天,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揭牌。
凌家滩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落,到如今成为融科研、教育、文旅于一体的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离不开考古人30多年来的接续努力。

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航拍图。胡成超 摄
1985年冬日的一天,马鞍山市含山县长岗乡凌家滩村村民万传仓在给去世母亲安葬时,意外发现许多石器、玉器,立即报告给当地有关部门,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后派专家赶往调查,并于1987年6月进行了第一次考古挖掘。
1987年,张敬国带队进行首次发掘;21年后,吴卫红开始新的十年探索;2019年,张小雷在“考古中国”和“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两大课题下接续发掘......考古人通过自己的手铲一点点为我们揭示出凌家滩遗址的生动面貌,在“何以中国”的文明探源中落下重重的棋子。
凌家滩遗址考古发掘第一阶段
时间:1987年-2007年
领队:张敬国
“璀璨星光———凌家滩文化展”在安徽博物院新馆开展以来,一直观众如云。我们有幸在凌家滩考古工作队第一任领队张敬国的解说下参展。“仿佛重回当年的考古现场,很多情景历历在目。”张敬国不时感概。
遇到凌家滩时,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张敬国已经从事田野考古10多年,跑遍了淮河两岸和长江南北。遇到凌家滩后,他的名字便和这个5000多年前的文明绑在了一起。1987年至2007年,张敬国带队在凌家滩遗址先后进行了五次考古。

张敬国(左一)在考古发掘现场做介绍。图片由本人提供
“那时长岗乡还未通汽车,从太湖山到长岗乡有5里路,我们扛着几十斤重的行李,走了足足两个小时才到。”张敬国回忆,他们住乡政府对面的招待所,在乡政府食堂搭伙。乡政府距考古工地也是5里路,每天来回四趟,一天要跑20里。
他始终清楚地记着正式发掘第一揪土的时间:1987年6月12日上午9时36分。第一次发掘面积只有两个探方、50平方米。由于文化层较浅,揭去耕土层和很薄的汉代堆积后,很快便发现了早期墓葬。后来命名为87M1的墓葬首先发现了3 件国宝级文物“站姿玉人”。“只能用别开生面来形容。”时隔30多年,回想起当时,张敬国依旧掩饰不住激动。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人。图片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玉人以浅浮雕技法制成,体态比例匀称,是我国发现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人体玉雕塑。玉人头上雕刻出的冠帽、身上的装饰,表明先民们已经掌握了纺织技术,懂得美仪表。祈祷的姿势,彰显着凌家滩人远古崇拜的观念。随葬玉人是一种代表身份和地位的高等级礼制,说明了那时的聚落已经有一定的礼仪。
“之后,我们又陆续挖出三角形刻纹玉片、玉勺等玉器,最令人兴奋的是发现了其它遗址从未见过的刻纹玉版和玉龟。”张敬国介绍,玉龟分成了上下腹甲,腹甲做得非常逼真,在上下龟甲之间有几个孔,应该可以用绳子拴上。玉版光素无纹,两面均抛光,正面刻纹,中部一小圆,内琢刻八角形纹。小圆外琢磨一大圆,大小圆之间以直线平分为8个区域,每个区域内各有一条圭状纹饰。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龟。图片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版。图片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这是非常重大的考古发现,甚至是改变历史的发现,古人的精神世界就这样直观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显然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了。”张敬国说,“直到今天,对于玉版和玉龟的讨论还在进行着。”
第一次发掘后,张敬国在当地举办了3天的小型成果展,让当地村民和附近十里八乡的人一饱眼福。“还有人专门从合肥赶来,凌家滩从未这么热闹过。”
当年11月,国家文物局又批准进行600平方米的发掘。第二次考古发掘中最重要的发现是命名为M15的墓葬。“墓葬主人胸前挂满了三十多件玉璜,这在新石器时代墓葬中是独一无二的。”张敬国说。
第三次考古来得有些晚,时隔11年后于1998年重启。这次考古探明了以凌家摊遗址为中心、半径约2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6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1处大型墓地,系一处规模较大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聚落群。在凌家滩墓地中心的最高处还发现新石器时代祭坛一座,面积约600平方米,一个布局完整的史前文明日渐清晰。当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公布时,凌家滩位列其中。
随后,张敬国及其团队在2000年和2007年又对凌家滩遗址进行了发掘。凌家滩遗址考古工作队第二任领队吴卫红从1998年开始参与凌家滩考古,对2000年和2007年的两次考古如数家珍。

吴卫红在考古挖掘现场。图片由本人提供
“第五次考古中发掘的07M23墓葬,是凌家滩历年发掘墓葬面积最大、出土遗物最丰富的一座墓。玉器200件,石器近百件,墓葬底部铺满石锛和凿,胸部放置多件玉钺,以玉钺覆面,这无疑是等级最高的王。”吴卫红介绍,这个墓葬还出土了3件玉龟斜口扁圆形器。玉龟巴掌大小,中空,器壁较薄,与玉龟一起出土的有一枚扁长条形的玉签,玉签上还有两道刻痕。“这可能是中国发现的最早有刻画符号的玉签,可能是作为占卜使用的,说明了凌家滩精神文明达到的高度。这让我们想起87年出土的玉版,几乎就是最完美的呼应。”
张敬国任领队期间,共主持了5次考古,发掘面积2960平方米,发现大型祭坛1座,墓葬68座,出土玉器和玉料1100余件、石器600余件、陶器500余件。在张敬国看来,凌家滩玉器、红山文化玉器、良渚文化玉器,这些具有观念意义的特殊玉器群的出现与广为流行,并非偶然,它是中国文明形成的一个里程碑。
凌家滩遗址考古发掘第二阶段
时间:2008年-2018年
领队:吴卫红
“前五次考古可以说是凌家滩耀眼的红花,但还需要更多的绿叶来支撑。第一阶段考古解决了一些问题,也带来更多的未解之谜,比如凌家滩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这里和周边是什么关系,是一枝独秀还是众星捧月?如何构建一个区域的社会图景?我们需要了解遗物与遗迹的关系以及社会发展的动因等等。”2008年,吴卫红领队在凌家滩遗址开启新一阶段考古。
“当时国内已经从器物考古走向聚落考古,我们提出了‘由玉器到聚落’‘探寻活着的世界’的工作理念。2008年开启第一步,先是方圆5平方公里,后来扩大至20、30平方公里,遗址的主要分布范围用5米间距进行广泛钻探,外围文化堆积稀疏区为10米间距,更外围是20米间距。”在吴卫红看来,只有进行了全面的调查,才会产生出许多学术上以前没有的线索与思路。

吴卫红(右一)在考古现场进行勘探。图片由本人提供
这是最笨的办法,也是最踏实的办法。术语称之为“不留空白式”区域调查。这种调查需要充足人手,于是,吴卫红在网上“广发英雄帖”,公开招募志同道合的考古人,主要是各个高校考古专业的学生。这让他招募到一批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如今也成为行业内公认的行之有效的操作方式。“每次10个人左右,持续进行了8次区域系统调查,基本摸清了这个区域的聚落遗址分布和考古文化分布,知道了凌家滩文化不是无源之水,它与同处长三角地区的崧泽文化、北阴阳营文化一脉相承,也知道了它直接影响到之后的良渚文明。”
2008年至2013年的工作卓有成效。对凌家滩及周边400余平方千米进行了区域系统调查,发现近20处小型聚落,年代大多数略早于凌家滩,反映出较明显的聚落集中化趋势。同时对凌家滩及周边10个遗址进行全面勘探,勘探面积超过200万平方米,发现了内外两重环壕,在岗地东侧的石头圩发现大面积的生活区。

凌家滩遗址上的内壕遗迹。 李俊杰 摄
2009年,凌家滩作为区域核心性遗址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课题研究。 2012年12月在含山县召开中国凌家滩文化论坛,正式命名了“凌家滩文化”。“凌家滩文化的出现开启了一个崭新时代,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曙光,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具有标志性地位。”吴卫红说,“这样的定语来之不易。”
2013年和2014年,吴卫红及其团队对石头圩生活区、内环壕西段和北段缺口处进行了2次主动性发掘,发掘面积约600平方米,确认了均为凌家滩文化时期的遗迹;2015年至2017年,结合考古遗址公园的展示和工程建设,在外环壕西北段、防洪工程所涉范围进行了发掘。
2018年后,吴卫红离开考古一线,成为安徽大学历史学院的老师,在课堂上向更多的学生传授考古学知识,也有更多的时间对凌家滩进行深入思考。刚刚出版的《凌家滩:中华文明的先锋》就是他思考的结晶,“凌家滩文化中晚期,创文明新风、创复杂礼仪之要、创玉器工艺之先,已具备了相对复杂的社会结构,在诸多文明要素方面都有自身独特的贡献,是从原始社会到古国阶段的关键节点,具有标志性地位。”
凌家滩遗址考古发掘第三阶段
时间:2019年至今
领队:张小雷
在凌家滩遗址考古工作站,记者见到了现任领队张小雷及其团队。拍照、修复、绘图......十来名工作人员正紧张地忙碌着,一旁,张小雷坐在电脑前,撰写考古简报,不时起身,查看团队工作进度。
凌家滩是“考古中国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课题”在安徽地区的唯一发掘地点,作为长江流域的重要区域中心聚落之一,于2020年被纳入新一轮中华文明探源研究课题。同年,凌家滩考古再次启动。
这不是张小雷第一次参与凌家滩考古。早在吴卫红进行的第五、六、七次区域调查中,已经有他的身影。“和过去相比,我们工作生活的条件都得到了改善。”张小雷介绍,凌家滩遗址考古工作站所在的位置是以前的粮站,前些年,当地政府将原有的五栋大粮仓进行整修,实现了再利用。“现在,从宿舍到工作区,步行只要几分钟,方便了不少。”

2020年-2022年发掘位置图。图片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2020-2022年,我们对岗地东端的大型红烧土遗迹片区、墓地西侧以及外壕北段进行了发掘,出土不少器物,有石器、玉器、陶器等。”指着一块宽扁形石器,张小雷告诉记者,这是凌家滩目前发现的体量最大的一件石钺,长38.3厘米。除此之外,他们还发现了凌家滩目前出土的最大的玉璜。

凌家滩目前发现的体量最大石钺。 图片来源于安徽日报

凌家滩目前出土的最大的玉璜及一些玉块、玉璧。图片来源于安徽日报
出考古工作站,记者跟随张小雷来到了墓葬祭祀区西侧广场。现场搭建的大棚中是一个祭祀坑,也是本阶段发掘的重要发现。“在这里,我们共挖掘出各类遗物260余件,其中石器140余件、玉器70余件、陶器40余件。”张小雷说,石器多残碎,但多数可以拼合,并有少量完整器。器形以石钺占绝对多数,拼合后有完整的石钺60余件,另有少量石锛。这些石器大多被烧过,器体多已白化,部分石钺被烧变形。玉器多为残碎小型饰品,器形以玦占绝对多数,另有玉钺、玉管、玉珠、玉璜等,还有一些新器形,如齿轮形器、椭圆形牌饰、梳形器等。陶器位于坑内西端,以泥质红陶为主,少量夹砂红陶、白陶,有杯、鬶、鼎、壶、大口尊等,其中2件葫芦形彩陶壶较有特色。
这处祭祀遗存的发现,为研究复原当时的祭祀场景提供了资料,完善了对墓葬祭祀区布局的认识。出土的200余件遗物,丰富了凌家滩陶器、玉器的种类。部分特殊玉器的出土,对研究中国史前用玉制度及其对历史时期礼制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

张小雷向记者展示挖掘出土的石器。 李俊杰 摄
岗地东南端的大型红烧土密集遗迹片区中,张小雷团队用三年时间进行了2000平方米的揭露发掘,确定了该大型红烧土遗迹的范围、结构、堆积和年代,初步认为该大型红烧土遗迹年代为凌家滩文化最繁盛的时期。“以大型红烧土遗迹为代表的大型公共建筑的发现,深化了对凌家滩聚落布局的认识,证明凌家滩存在超大型的高等级公共礼仪建筑,并有明确的祭祀功能。”张小雷说。
记者留意到,采访过程中,一向话语不多的张小雷像是打开了话匣子,想把三年来全年无休的挖掘工作和新发现一一向记者道尽。在张小雷看来,对凌家滩遗址的三次挖掘中,第一次是发现凌家滩,第二次是揭示遗址的聚落布局,而他的工作则是对聚落中的关键点进行细致发掘。
眼下,周末的时候,张小雷经常会被附近的中小学请去进行“何以凌家滩”的讲座。在他的描绘中,凌家滩先民的生活图景很是清晰:5300年前,人们在这里从事稻作农业,兼养殖、渔猎和采集,同时从事玉石器与陶器制作、纺织等手工业生产。居住区有逾200平方米的建筑物,内外两条环壕堪称大型水利工程,原始宗教活动在大型祭坛举办,公共活动在红陶块广场进行……
唐军是凌家山县宣传部提供滩管委会的“元老”,前不久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联盟联席会议中获得了“杰出贡献人物奖”。如今两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挂牌,他最为欣慰。“原来占压遗址本体的5个自然村、约1000户村民顺利搬迁,考古人可以在公园内安心进行主动发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