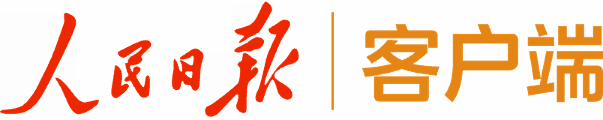在海岸与沙滩之间,红树林是一种有着独特生态魅力的存在,在抵御台风大浪侵袭、高效存贮海岸“蓝碳”及加速滩地淤高和向海伸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受限于红树林修复生境改造、定植空间及育苗等技术瓶颈,南方一些地区进行了红树林生态修复,但成效并未达到预期目标,红树林成活率极低,有的甚至存在“第一年种苗,第二年死大半,第三年所剩无几”的“魔咒”。
为此,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戴志军及其团队携手北部湾大学教授黄鹄、王日明,经过10年潜心研究,在红树林苗木培育、移植栽培、种植地生境改造与种植后养护技术等方面取得原创性突破,攻克了红树林生态修复的技术瓶颈,推动了科研成果转化助力绿色发展的步伐。
“红树林很有灵性,有极为罕见的植物‘胎生’,能在潮汐涨落中屹立不倒,我常常把它看作海滨守护精灵。”戴志军说,“随着科研与实践的深入,我们有理由相信,曾经受损的红树林生态系统将逐步恢复生机,为沿海地区的生态平衡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力量。”戴志军表示,这不仅是对自然环境的修复,更是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
2013年7月,戴志军第一次踏上广西茅尾海这片全国最大、最典型的岛群红树林区,发现该区域岛群蚀退严重,大范围红树林因树根裸露而倒伏,成活率较低。
在深入开展实地考察,并与护林员交流后,戴志军发现问题所在。他说,“红树林定植是世界难题,一是生境家底没摸清,二是通过立管、无纺布种植等技术,营林成活率低于50%,富集污染的虾塘营林率更低于30%。”
通过对不同省份数十个人工定植红树林的长期蹲点考察,研究团队发现出现“魔咒”的根本原因之一是红树林根系受到损害,初种时树叶绿油油,只因其可依靠消耗体内营养而保持良好状态;第二年大部分叶片变黄色,部分凋零,原因在于受损根系难以提供充足的养分满足植株正常生长需要。
为验证这一观点,团队成员王日明教授采集了上百个不同年龄的人工苗,发现第二年的人工苗部分根开始发黑,第三年则完全腐败变黑。
团队另辟蹊径,提出了本地红树林胚胎大钵育苗、根系无损移植与聚集定植的营林新模式,成功研发可抵御波流联合动力影响的“胚胎-幼苗”栽培方式,不仅提高了红树林成活率,同时也拦截漂浮水体的红树林胚胎,使其着床发育,缓解苗木数量匮乏与补种的问题,为红树林规模化种植提供保障。戴志军把这一团聚结构比喻成“抱团取暖”。
将原有红树林栖息环境改为养殖塘,是我国红树林面积减少的重要缘由之一。但是,将养殖塘“退塘还林”,其难度与复杂程度远高于宜林裸滩的红树林营造。
针对这一挑战,戴志军在孔雀湾高位虾塘实现“高能”的科技成果转化,将“动力、沉积、地貌、生态”四个要素有机结合,带领团队独创性地构想出“虾塘适宜红树林定植的客土甄选”“近自然滩-沟系统塑造”及“抱团取暖式红树林移植”等成套技术体系,并由此修复了钦州湾金鼓江孔雀湾废弃虾塘80余亩,定植的红树林历经三年仍保持成活率95%以上,可节约红树林保护修复总投入30-60%,创下了“孔雀湾奇迹”。
在海平面邻近区分布有广泛低滩,能否在广袤的低滩非宜林区种植出红树林呢?团队在广西最大的河口南流江出海口的七星岛进行了十几次科研实验,提出基于滩地水沙变化进行竹垄设计,创建红树林前缘低滩宜林生境的创新观点,并研发出近自然红树林生境改造与生态修复技术。他们设计的竹垄不但将低滩淤积速率提高约1.5倍,竹垄间距可成为爬行动物的生态廊道,竹垄则拦截悬浮于水体的红树林胚胎,让其沿竹垄发育成林。
该技术通过三年实验,已使南流江口约180亩非宜林低潮滩都生长了纯自然红树林,极大地节约人工种植红树林成本,成就了低滩非宜林地成林的“七星岛模式”,还被应用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平陆运河出海口沙井岛的红树林修复与非宜林地营林。

生长良好的红树林。戴志军摄

研究团队在平陆运河出海口沙井非宜林地改造实验现场。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