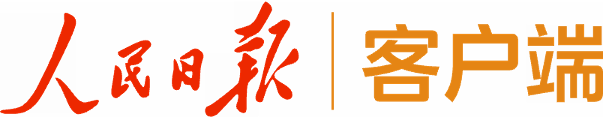原标题:冬至
在南方,冬天的到来总是显得珍稀。冬至有一年最长的夜,不单被称为冬节,地位还堪比过年。小时候老人会说“吃了冬节丸就大一岁”,让我以为冬至这一天的汤圆有什么加速时间的魔力,但其实不过是普通的糯米丸子。潮汕话“丸”与“圆”同音,冬节丸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家人团圆。大概寒冬已至,亲人们需要抱团取暖。搓汤圆是最热闹的,老人女人小孩围坐在一起摆弄糯米团,揉搓成小丸。潮汕地区的汤圆没有馅,手搓的实心汤圆大小不一,加红糖煮至绵软,比较讲究的人家还会加老姜调味,吃起来甜而不腻。冬至的汤圆放凉了看起来像一锅黏稠的蜂蜜,重新加热容易粘锅,发出甜甜的焦味。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这股焦味,闻来令人心情愉快。现在想不清楚为什么如此简单的食物,在童年竟会令人期待。
冬节前几天还会“筅囤”,也就是大扫除。这大概是为了冬节的祭祖做准备的。在潮汕地区,清明扫墓是“挂春纸”,冬节扫墓是“挂冬纸”。一般老人去世之后的前三年必须“挂春纸”,三年之后才可以“挂冬纸”。清明时节雨纷纷,冬节要比清明天气清爽,更适合登山扫墓,追忆似水流年,落日在寒风中也变得温柔起来,没有了炎夏的火辣之气。我对家里扫墓的记忆,从白毛公(外公)宣布不再扫墓那一年便空白了,依稀只记得山路泥泞,天气很冷,也不知道是春寒料峭还是北风来袭,还记得我有一只拖鞋掉落在草丛里。总之后来冬节便只是在家里拜祭了。
时光流转,岁月惊心。那些被日升月落所抹掉的日子,仿佛一张张被丢弃的废纸。而怀旧的人,仍然愿意在记忆里去重新创造它,认为它们一直都在那里,并认为某一天还能穿过时光之门回到过去。在时空的变换之中,我们还用内心的感念去生成活着的轨迹,我们依旧要为流年的逝去感到痛惜,为接踵而来的人和事惊喜不已。在浩瀚的宇宙之中,我们卑微如蚁;满天星辰,也不过是亿万年前的一场幻觉。确定一个意义是如此困难,不确定才是宇宙的真相,而我们却一直在坚持为自己建立意义之塔。我想,这大概就是冬至、春节、元宵这些“标志”存在的意义。节日成为锚定生命重量的工具,成为时空中的光标。

这几十年有许多潮汕人聚集到珠三角打工,我们一家也加入了迁徙的洪流中,从韩江边到珠江边,已忽忽20年了。原来父母在家里还有一个豆腐作坊,后来停掉了;种了两亩豇豆,后来改种青枣树。几年前,父母终于离开故乡的泥土地,跟着我们到珠三角生活,照看孙辈。自此之后,凡是要祭祖的节日,父母便有了回老家小住几天的理由,那感觉有点像请带薪年假,在事由那一栏终于能填上无法反驳的理由。
母亲从天气开始变凉,便开始念叨着冬节回潮州祭祖之事。而对打工人来说,冬至真的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节气,它又不放假,我们凭什么记得住它?母亲掌握着我们家祭祖的一切仪轨。时年八节,三牲五果,这一切如此复杂,如何记得住?
“家里还有你阿嫲。”母亲说。
阿嫲是奶奶。阿嫲今年刚满百岁,是另一个能熟悉掌握拜祭仪轨的人。在我们村,满百岁的老人是要穿上红肚兜,游街走一圈的。但年初她生日时,家族的老人主张还是低调行事,免得惊动天地神明,知晓了她的岁数,于是启动了“静默模式”,就连生日都过得“偷感”十足。我的弟弟妹妹去陪阿嫲聊天,每个问题至少重复三遍。“哪天回来的?”这个问题会无限循环。可能在阿嫲眼里,我们突然出现在眼前,过些天又消失不见了,于是何时回家这个时间点永远也无法弄清楚。母亲常说,“你阿嫲是个机器人,坚固耐用。”阿嫲除了记性不好,其他方面真的像一部低能耗平稳运行的机器。前两年摔伤了手臂,我们都颇为担心,她却以神奇的速度痊愈,还偷偷领了手工在家做,赚零花钱。被我们发现后才像个犯错的小学生,说不做了。
阿嫲这个“机器人”,据说她一辈子的活动范围不会超过方圆50公里。她年轻时挑过盐,见过日本鬼子进村;从没有坐过飞机,却亲眼看到敌机的炸弹如何炸出深坑来。有一年春节,我开车带她到潮州古城转了一圈,回来后她说晕车,并连连摇头:“太远,太快。”那不过10公里的距离而已。仿佛她专门占领时间,却并不拥有空间。很多年前,她从另一个村越过一座小山丘嫁到这个村,从此便一直在这里。对于远近的理解,她的量词是“铺路”(里路),大概是用脚来丈量的路;而丈量远近,我们是用车轮。
圆形的冬节丸在召唤团聚,而同样圆形的车轮则注定了离别。小时候第一次骑上凤凰单车,那时我的个子跟单车差不多高,故此骑车的动作十分怪异。我的右腿得从三角形车架中间穿过去,歪着脑袋踩车,虽然我一次次摔得四仰八叉,却十分高兴,认为自己终于可以征服远方。10多年前我有了自己的第一辆汽车,停在楼下马路边,那天夜里我下楼3次,确认车的存在,总担心这辆手动挡汽车的4个车轮会被人拆走。这辆汽车第一次将作为出生地的故乡和让我成为异乡人的新家连接在一起,与绿皮火车和长途汽车相比,我拥有了一种随时回到老家的可能。
现在的汽车纷纷换成新能源汽车,不用加油,改用充电,广告里会将新能源汽车比喻成智能机器人。开着仿佛拥有智能的汽车在路上跑,车在巡航,而我沉浸在记忆里。我想起童年的汤圆,怀念去世的亲人。比如冬节清晨,白毛公会蹲在门口煮芋泥,他会在芋泥里淋上葱猪油,那是比汤圆更好吃的童年美食。白毛公的岳母,我喊她老嫲。6岁以前,是老嫲带着我睡觉,给我唱童谣。我有时半夜会被吵醒,发现老嫲在暗夜里啜泣,十分困惑。长大后才明白她在哭远在暹罗的丈夫和儿子。后来我写小说,查阅了很多往来的侨批,明白了人世间的离别。包括冬节在内的年节拜祭是海外潮汕人家书中频频提及的重要时间节点,这些远离家乡故土的华侨,会按照古老仪轨所规定的时间寄钱回家祭祖。也就是说,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成为异乡人,无法改变或切割某些看不见的文化记忆,并将原本属于潮汕的生活方式带到远方。
从潮州到广州,车轮滚滚,汽车广播里正在讨论登月计划,说再过几年中国人便要登陆月球,国产的机器人也会在月球上活动。此刻,月亮就挂在天空上,它的阴晴圆缺既代表团聚,又代表远方的离别。我能想象一个机器人站在月球上遥望地球,但愿彼时,它也能带着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