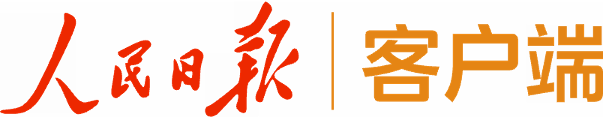原标题:喊叫水
去喊叫水乡的路,越走植被越稀疏低矮,野云低垂,大地的颜色也从土黄变成灰褐。房舍星散,原野上偶见一两棵树,长了许多年也长不大似的。喊叫水乡2004年从同心县划给了中宁县,中宁枕着黄河,是“近水楼台”,同心则地处干旱带。“划拨”是因为水!
宁夏地理风貌一分为二,黄河灌区素称“塞上江南”,其余多是干旱半干旱区,西海固是其典型代表。当年“旱海”连绵,一首“花儿”唱怨:“六盘山石硬又硬呀个,蹦不出半滴水啊,黄河水从后山拐了个弯儿呀,硬是不肯回头走……”
喊叫水乡过去苦焦更甚,光听名字就让人咽唾沫。传说宋将穆桂英带兵追击辽军来到这里,几天几夜也走不出荒漠,人马干得冒烟了,却找不到一汪水。眼见要全军覆没,一匹有灵性的战马在地上猛刨,不一会儿,沙窝里有了潮气。三军大喊:“水!水!水!”此刻清泉涌出,喊叫水由此得名。当地人说这泉便是石泉,在一条古老的商道边上。
石泉在石泉村,一片坡地上,杂草丛生,泉水从砾石间渗出,漫溢开来,又聚成蓝汪汪的池水。只是已经荒废十来年,很难想象此前村民们来打水的状况:一字长蛇排队,骡马嘶鸣。我用手指蘸泉水尝试,唇齿淡淡咸涩,味似以前的日子。
那时候,石泉的水越喝越渴,肚子里咕噜咕噜翻腾,还得省着用。人们用泉水掺着窖水吃,窖水来自收集的雨水和融化的冰雪。炒菜为了省油,拿“油袋子”在热锅上抹一圈,常常半月不见荤腥。石泉村党支部书记金文龙兄妹三人,小时候母亲骑自行车驮着他们去远处抓发菜,身前坐一个,身后坐两个,路那个颠呀……
冯秀花和金文龙母亲年龄相仿,她家在喊叫水挺有名。1997年,“上面的领导陪着福建的客人”来到她家,但见家徒四壁,梁上挂着撮换钱的发菜;一孔箍窑屋顶漏了,用塑料布遮盖。客人们嘘寒问暖,走时留下2000元钱。家里用这钱盖了两间房,如今这两间房已换成一排大平房,生活也“从地面到太空了”。多年后冯秀花才知道,闽宁协作伊始,春风便入她家。
如今冯秀花的儿媳妇丁燕,年龄和她那时相仿。丁燕肤色黑红,身形微胖,开口便笑。她和老公领着4个娃,平日在周边农业基地打工。喊叫水乡的田野里,水果玉米、贝贝南瓜、葵花子、硒砂瓜比比皆是,只要不懒,都有活干。
能有这么多打工机会,全靠黄河水。冯秀花在家当姑娘时,老辈人说,喊叫水能喝上黄河水,除非黄河倒流!可不是,黄河在上百里外淌着哩。明知不可能,心里却忍不住想,喊叫水人就在地名上做起“文章”:长流水、鸭湾子沟、红柳湾子、大滩川。他们梦里头的“西海固”,是个水网交织的“塞上江南”。
黄河的确不会倒流,但黄河之水天上来!50多年里,腾空而起的扬黄灌溉工程,把黄河水越送越远,如今都到西吉县啦。刚通水那会儿,不少人爱跑到渠边看水:清波漾漾,丝丝绿绿的,顺着“双眼”流进“身体”……欢唱的黄河水流到哪里,哪里就生机焕发,浇庄稼都和苦咸水不同,绿油油的不咋生病,真个赛江南!
不过,水来了后也有烦恼。以前撒下种子等雨,不用平田整地。换了水浇地,都不会种了,看黄河水在地里横冲直撞,小媳妇急得哭。近些年漫灌变滴灌,“老把式”也看不明白了:这么弄庄稼能喝饱?新事物接踵而至,生活的波澜荡开又平静,喊叫水人一天天见识多了,鸡毛蒜皮、你争我夺的少了。在北沿口村民马秀廷家谝闲,桌子摆满馓子、油香、苹果、核桃、开心果。老马认为大家心宽了,说到底是日子好过了,犯不上太计较。在村里走走转转,家家户户是红顶新房,太阳能路灯、水泥路有了,种下的树苗长开了,从脱贫到乡村振兴,有啥不知足的。
早前每逢下雨,各家集雨场上先除草打扫,谁家水路多水窖多,就好讨儿媳妇。如今一块块集雨场都种上了树,水窖基本集体“下岗”,水路旱路都成了硬化路。我发现,各家新房的房檐下,依然接着不锈钢水槽,雨水引入留作纪念的水窖,浇花种菜。原来喊叫水人骨子里惜水,加之地基是湿陷性黄土,房子盖大了,若房檐水淋漓直下,的确不科学。
离开喊叫水乡时,四顾苍茫,想起一句“水咸草枯马不食,行人痛哭长城下”的边塞诗。大地深处,历史正在悄然改变色泽与温度。喊叫水不只是个地名,念念不忘中,不知不觉唇齿生津,回甘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