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分子生物学与高通量测序技术的迅猛发展,古DNA(ancient DNA, aDNA)逐渐成为当代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工具。古DNA是指从古人类遗骸、动物骨骼、植物种子或沉积物中提取的高度降解的遗传物质。相较于传统依赖器物、骨骼形态与文化遗存的研究路径,古DNA提供了一种直接揭示古代人群遗传构成与动态的全新方式,使得对人类演化史、迁徙路径以及人群互动等问题的研究更具分辨率和实证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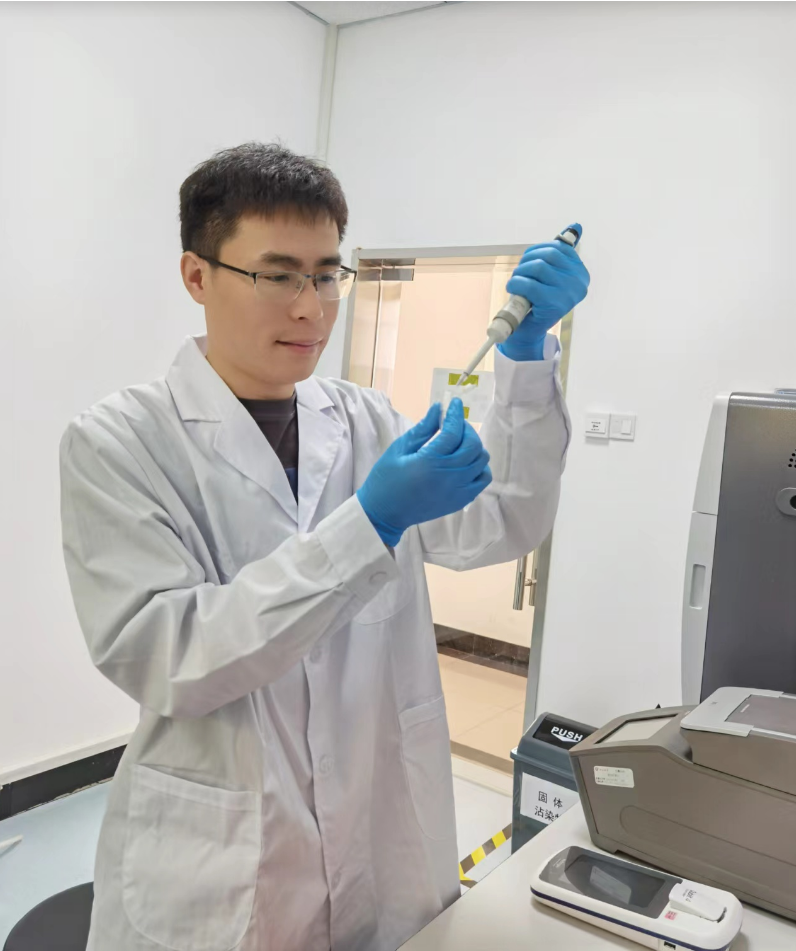
本文作者宁超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分子考古学、分子古病理学研究和分子法医学研究
在考古人类学研究中,古DNA的最大贡献之一是对古代人群起源、扩散与交流模式的重建。通过与现代人群基因组的对比分析,研究者可以追溯不同人群之间的亲缘关系、分化时间与基因流事件,并据此推断人群迁徙的方向与过程。此外,群体遗传结构分析还可揭示古代社会中的族群融合与边界动态,为理解考古学文化间的异同提供生物学支撑。在与语言学和考古学证据交叉验证的基础上,古DNA成为揭示深层人群历史的关键证据来源。除宏观人口历史外,古DNA亦广泛应用于微观层面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制度研究。利用高通量基因组数据可识别同一墓葬个体之间的亲属关系,从而推断家庭结构、婚姻规则与居住模式。结合性别判定与单倍群(Y染色体与线粒体)分析,还可以揭示父系或母系继嗣方式、性别分工与族属认同。此外,在与稳定同位素、骨病理学等多学科数据整合分析的基础上,古DNA也有助于识别社会等级差异与身份认同机制,从而拓展对古代社会组织的认知。古DNA技术亦显著推进了对古代人类健康状况与生计模式的研究。通过识别古代病原体DNA,可以追踪历史时期疾病的传播路径与流行动态,甚至探讨人类免疫系统的适应演化。另一方面,不同经济模式(如农业、牧业、渔猎)下人群的遗传差异,也为理解技术传播、生态适应与文化变迁提供了遗传学视角。与此同时,动物与植物的古DNA研究亦揭示了家养物种的驯化历史及其与人类迁徙的协同演化过程。

首次用分子人类学与遗传学为证据对傅家遗址进行新的研究,为探源中华文明找到“技术路线”。图为研究人员在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DNA实验室进行构建古DNA文库实验。
综上,古DNA的引入进一步拓展了考古学的研究边界,使得对人类过去的探讨从物质文化维度延伸至遗传谱系层面。它不仅重塑了我们对史前人群结构与互动方式的理解,也深化了对社会制度、疾病生态与生计演化等核心问题的探讨。未来,随着方法学不断优化与伦理实践的规范化,古DNA将继续在全球范围内的考古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考古学从传统描述向综合解释与机制揭示的转型发展。
(作者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员)

来源|《北京大学校报》1696期第3版
责编| 李舒燕
